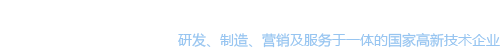当时余震频发,我们从彭州通济的山里出来,转场到鸡冠山。已经吃了几天方便面,我特别想找一个打牙祭的地方。恰巧路边有一间房子,门框上用油漆写着“三妹子酒家”,没有犹豫,我们停车钻了进去。饭馆没有菜谱,所有的原料都摆在明面上。大厨是个粗壮的中年汉子,胡子拉碴,手里攥着莱刀拍拍打打给我们点菜。我们要了一份粑粑菜、一份老腊肉, 便坐下等着。
不一会儿,菜端上来(叫扔上来更准确),第一口咬下去,不由得转身对老板“伙计,你家腊肉太咸。”正在刷锅的老板头都不抬:“只有这个。”什么态度嘛,我心里想。第二口,却吃出一股奇香,仔细再看筷子尖上的物事,大片的腊肉,由外至内,从深褐到鲜红——显然是暴腌暴晒过的。旁边搭车的一个彭州哥们儿说:“这家的腊肉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。要不是地震,还可以吃到他家的风干鸡。我一边吃着菜,一边再看那个中年汉子,隐隐地在心里生出了“世外高人”几个字。这就是所谓的江湖菜吧。
我仔细做过研究,原生态江湖菜一旦离开故土,原料、作料的供应都不可能似以前充足地道;另一方面,在陌生的环境,面对全新的客人,大厨下手时不免要多看看顾客的脸色,做很多让步。众口难调,味道不兔中庸起来,原先支撑做莱的某种理念也开始动摇。在城市餐饮激烈竞争的环境里,大厨的脸色,很难像彭州乡间的那个汉子一样自信。
社会信息化程度愈高,大众的趣味愈发趋同。然而,菜肴个性化和餐饮业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永远无法同步。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以江湖菜扬名立万的馆子,慢慢地,“江湖””两个字只剩下商业意义上的招牌意味了,
如果把烹饪比心江湖,我最喜欢的厨艺高人当如风清扬——背负绝学,遗世独立。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三两知已,绝不会参加武林大会之类有套路、规则的选拔。他们做的菜永远是小众的:有性格,意气风发,绝不会考虑劳什子评委渐渐迟钝的味蕾和已经退化的牙齿。
当然,这种念想实现起来越来越难——你看嘛,金庸都进作协了。